/0/52604/coverbig.jpg?v=a3d64fedb55cd78a246a67bd79c71e13)
/0/52604/coverbig.jpg?v=a3d64fedb55cd78a246a67bd79c71e13)
正文 暗湧(一)
散了早朝,文官武將紛紛散去,李隆基隨著眾人走出武城殿心情十分複雜,今天又是例行請安的日子,他不像外臣除了宣召不得擅自入內,他需定期向那個本是他皇祖母的人定期請安,一如他有著郡王的封號不用像別的大臣走旁道一樣,這一切在外人看來都是無上的榮耀,可誰人又知這榮耀背後所付出的代價。
世人都說帝王家的孩子早熟,安穩無憂的人才有天真的資本,外人只知羨豔他表面的光鮮亮麗,卻不管這光鮮背後的血淚。如果可以他寧願自己只是一個尋常人家的孩子,這樣面對祖母多少還能享受些天倫之樂,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每一次面聖他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可以,他多想立刻掉頭而去,天涯海角遠離這裡,越遠越好。可惜從十四年前開始,他便無從選擇,那年他才五歲,本不該有太多記憶,或許是這些年刻骨銘心的苦痛將那日的情景一刀刀刻入血肉,再也無從忘記。
那一年好不容易熬過了大唐立國以來最漫長的夏季,孰知相較於往後的日子,那場酷暑,竟那麼讓人戀戀不捨,結束那場旱季之後的第四天,一個秋高氣爽,碧空萬里的日子,父皇,帶著全家早早等候在則天門門樓外凹形空地,卻差點被人海淹沒,似乎這刻整個東都之人都擠在這裡,門樓前縱橫交錯的是皇親國戚、王公貴族、文官武將、四夷使臣、金甲武士、歌女舞伎,人頭攢動,香汗淋漓,各個面露喜色,鼓樂之中,頭戴朱紅花冠,身著黃色袞袍,腰系十三孔金玉帶的皇祖母立在那一百二十尺高的城門上,從納言手中接過玉璽,那時的他還並不清楚這一切的涵義,只是皇祖母明黃袞服上被九龍簇擁的七色神鳳,在父皇的眼淚中振翅欲飛,那個一向溫和的父皇,在眾人的洋洋喜氣中悄然落淚,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他不懂。
他不懂,他還不甚清楚,為什麼皇祖母變成了皇上,這大唐如何變成了武周,李家的天下怎麼就成了武氏的江山?所以七歲那年的出言不遜,那日朝堂的祭祀,他因看不慣那人在祖宗的地方吆五喝六,斥責了金吾大將軍幾句,當著眾人皇上並未發作反而誇讚幾句,當他把這個消息洋洋得意得告訴母妃,母妃卻流淚抱著他說大禍將至,那一刻他不以為然,他暗地裡嘲笑著母妃的膽小與怯懦,然其後的日子證明,母妃用性命與聲譽證明了自己的遠見。
果然,長壽二年正月初二那天,新年剛過,皇嗣府院中掛滿了倒貼著福字的大紅燈籠,在新年的洋洋喜氣裡,府中幾個小輩齊約去給長輩請安,父王滿意的喝著他們敬的茶,連平日裡難得對他和顏悅色的皇嗣妃都笑盈盈的遞過新年紅封。這時突然一群太監帶著上諭帶走了母妃和皇嗣妃,在人群中他依稀看見了皇嗣妃的婢女團兒,眾人愣在當場來不及反應,母妃卻趁亂將他緊緊抱在懷中摩挲一回後又鬆開,那時他並不懂母妃眼中那化不開的悲傷。
誰也未曾想過那一面竟是永訣,自那日起,他再也沒有見過母妃,過了好些日子他才知道,原來是團兒告了禦狀,說母妃和皇嗣妃挾蠱道詛咒皇上,皇上當即雷霆大怒,將母妃和皇嗣妃詔進宮——絞殺!
那個案子當時影響頗大,一時之間李氏一族人人自危,誰亦……不敢多置一詞更遑論替她們求情。可笑這樣的一個驚天大案疑點卻疑點重重,為何僅僅一個皇嗣府的下婢竟可以直達天聽,而皇上竟只憑一個婢女的隻言片語就將皇嗣的兩個妃子處死,更不用提平日裡眾所周知,皇嗣妃一向與母妃不睦平日裡更是對母妃百般挑剔,這樣的水火不容的兩個人竟能湊做一處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可謂奇矣!然這樣疑點重重的案子卻在皇上的金口之下塵埃落定,他甚至連母妃的屍首都見不到,他在皇上長生殿外的院中跪了一日一夜,得到的不過是臨淄郡王的封號。
也因此,他們開始了在這深宮之中近十年的幽禁,十載光陰,朝不保夕的日子,他有大把的時間將一切慢慢想清楚。他終於能讀懂父王欲言又止的眼神,族人怨恨的眼神和皇上深不可測的眼神中的恩威並施,無需任何證據處死母妃不過是對他的告誡,這江山早已姓武,她才是這江山的主人,李氏一族的性命在她眼中賤如螻蟻;而在處死母妃之後封了他臨淄郡王,是施恩予以安撫,他終究還是她的孫子,只要他做一個安份的傀儡他仍可以享一份榮華。母妃用血和性命換他長大,從那之後,他便開始收斂起所有的情緒謹言慎行,做起他的閒散郡王,他深知母妃用性命換了他一次的無心之失,若再有一次,必定死無葬身之地!
他背負著那個染透母妃鮮血的封號,便背負母妃的性命與希冀,他學會了收斂所有情緒,學會雲淡風輕,他唯有努力活下去才不會辜負枉死的母妃,所以他每次面對深宮中的那個人,不能再踏錯一步,因為一步踏錯便是萬丈深淵,萬劫不復!
日後每當有人提及那個染透母妃鮮血的封號時,他無論如何痛徹心扉,都只能將一切埋葬於心底。
收拾好情緒,李隆基向前走去,再過一道宮牆長生院就能望見「站住」一把利劍先於那相當無禮的聲音攔住了李隆基的去路,索性他走的不快,否則定會被那利器所傷,李隆基抬眼望去,面前那人是新進的北衙禁衛的統領曾賢,此人四十出頭,長相倒是周正,一身禁軍服倒也襯得十分挺拔魁梧,但李隆基一向十分不喜此人,只因這人一雙眼十分邪氣,當他隨意轉動雙眸時總讓人覺得此人不懷好意。
見李隆基停在光順門前,那人發出意義不明的一聲輕笑「原來是臨淄郡王,恕小人一時眼拙未看出來,得罪了。」
李隆基聽出他語中的輕慢,心下了然便道「曾統領何出此言,這原是曾統領是職責所在,豈有怪罪一說。」
「郡王今日可是奉召入宮」曾賢上前一步堵住李隆基去路。
「未曾奉召,今日不過是給陛下例行請安的日子。」李隆基心下對此人的厭惡又多了一層,面上卻不動聲色。
「曾統領原不怪你,你沒當過幾天差,自是不知道這太初宮的規矩。」後面一個爽朗的聲音傳來。
曾賢聞言臉上一片青白。
「王兄」李隆基聽見這個聲音,轉身含笑望向來人。
「走」李重俊一把扯過李隆基,毫不理會守門的禁軍大步向前,背後曾賢望向他們遠去的身影目中滿是怨毒的神色。
李重俊攜著李隆基前行,李重俊前幾日因事未去張府參加酒宴,後聽下人說起席間之事大呼過癮,這刻拉著李隆基問長問短,李隆基被纏不過只得將那日之事一五一十說給他聽,重俊聽李隆基親口說起,更是笑個不停,「可惜我不在,不然真想看看那兩人的臉色,哈哈。」
兄弟二人一路上說說笑笑,長生殿轉瞬就在眼前。互望一眼收起嬉戲的神色,二人恭順的立在殿門外,聽著內監的回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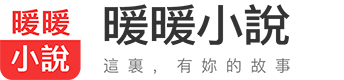



/0/93719/coverbig.jpg?v=7810b12b50268619b63264404d506cb0)
/1/130835/coverbig.jpg?v=a5f4143c7f102428a54c8c548dbabd38)
/1/130837/coverbig.jpg?v=495baa66096d93f001fc757989afd522)
/1/130838/coverbig.jpg?v=5fa488f67ee53a2dc14f6f9adcbf4824)
/1/130880/coverbig.jpg?v=98fc0c688944e7efeec4cffe99280b73)
/1/130882/coverbig.jpg?v=6f8a5a33e6361695bb670118b42fb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