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03/coverbig.jpg?v=875f14b8d5151dd418f7d9790268c12d)
/0/2203/coverbig.jpg?v=875f14b8d5151dd418f7d9790268c12d)
第2章 寒門貴子(2)
小姨說媽媽小時候很愛看書,那時候也沒什麼書看,能找到的寫著字的紙片她都很珍惜,去趕集,看到肉販子都是用報紙把肉包好給顧客,她就會請求老闆可不可以多包一層,然後回到家裡仔細的把報紙收好留著有空的時候看。親戚鄰居家糊牆的舊書雜誌報紙也是她的閱讀來源,去別人家做客,只要看到牆上有字她就會趴在上面看,不看完說什麼都不肯回家。
村裡人和外婆說,你閨女以後肯定是個搞學問的,鄉下人嘴裡說的學問人最終指向的是國家主席那樣的人物。說完又惋惜的歎口氣,緩緩的搖著頭,好像在親身體味著對面那個人的內心痛楚,說,可惜是個女孩。
外婆也不覺得女孩子搞學問是什麼大出息,總是跟人抱怨閨女的腦子有問題。
外婆有她的打算,她還有兩個兒子,老大和老三,兒子娶媳婦是家裡的頭等大事。自打她生下兩個兒子之後,就像螞蟻築巢似的一點點的積累著未來兒子結婚的資本。但不管他們兩口子如何辛苦操勞收入都是有限的,在農村可以產出的就是那麼多,想把兩升米放到一升的簍裡是不行的,需要一個更大的簍子,可是更大的簍子在哪裡?肯定不是在這個連出趟縣城都要走十裡地山路才能有公車的小山村裡。
此外她還有個更大的心病,大兒子有小兒麻痹,倒不嚴重,就是腿有些瘸,不影響走路幹活,但在這種條件下不容易娶到一個健康能幹能生的媳婦,她時常為此感到寢食難安。
簍子就是這麼大了,她可以盼望的就只能是大女兒將來能早點找個好人家,好人家是指能給得起一筆不錯的彩禮的人家,有了那樣一筆錢之後,兒子娶媳婦的資本就會變得雄厚許多。一個正常家庭裡,女孩都需要為兄弟做貢獻,天公地道,假如可能的話,寫入憲法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可是大女兒的心思從來都沒在找個好人家嫁了上面,她一門心思就是讀書。外婆為此感到焦慮,一個女孩子讀那麼多書有啥用?花上一大筆學費,幾年之後還不是跑出去再也不回來。一想到花了不菲的時間和金錢就是為了女兒將來貼外家的時候,外婆就一陣陣頭皮發麻。唉!如果兒子和女兒調過來就好了,真是天公不作美啊!
她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後,對小女兒的教育就是不停的向她灌輸女人一輩子最大的成功就是嫁個好人家,不能讓她像大姐一樣讀書讀到走火入魔。其實她的擔心有些多餘,小女兒書讀的很爛,也沒有多少心思在學習上,但這不影響她仰慕大姐,因為仰慕大姐的緣故,順帶著也很喜歡我,她早期難得拍的一些照片大多都是抱著我的。
小姨從不掩飾對自己母親的不屑和蔑視,在她眼裡外婆就是一個一個又一個的笑話集合體,說起那些笑話的時候總是一副聲情並茂的樣子,比電影還好看。小姨有趣,活潑,隨時能引爆沉悶的空氣,我真的太喜歡她了,遠勝過喜歡媽媽。現在再回想時,也許我真正喜歡她的那部分並不是她比媽媽能帶給我更多輕鬆的時刻,她與媽媽最大的不同是敢於反抗自己的母親,繪聲繪色的以嘲笑的方式把母親置於一個被批判的位置。
「那時候你外婆知道老師想讓你媽去縣裡上高中的時候,簡直瘋了,跳起來就往學校跑,鞋都跑丟了,就因為一個月要多花不到一百塊錢的路費和伙食費,到學校去跟老師撒潑,說老師沒安好心,我和我姐拽都拽不住,真丟臉。我看沒安好心的是她吧?」
「那我媽最後去縣裡上學了嗎?」
「沒有!」小姨氣鼓鼓的說。「可是在鄉里的中學不也考上大學了嗎?」
最後我媽還是沒有上大學,據說那時候鄉長都來了,那可是北京的重點大學啊。外婆拿出她潑婦的本領,把所有來勸說的人都給趕跑了,畢竟人家當官的都是文明人,拿潑婦是沒辦法的,最後上大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其實就算沒有小姨對外婆的種種批駁,在我很小的時候,兩三歲?反正從一個幼童在他能夠感受到外界施加到自己身上的是種什麼樣的情感開始,我就不喜歡外婆,因為我知道她不喜歡我。每個星期媽媽都要帶我去外婆家,一直到我五歲之後她外出打工。我不願意去,但不敢反抗,在爺爺奶奶家這邊,媽媽是一種神聖的存在,家裡的大事小情的都會徵求她的意見,「還是先問問雪梅吧!」或者「你不問問你媳婦?」這樣的話在家裡經常聽見,我不敢想像如果對媽媽的要求提出反對意見會怎樣。
也許根本不會怎樣,媽媽除了表情嚴肅還有爸爸那一家人所營造出的高高在上的氣氛,其他方面是很隨和的,從來不會強求孩子們必須要怎樣。
我對媽媽執意每週都要回去探望母親不能理解,我並不覺得外婆有多麼的歡迎她,到現在也不知道媽媽對外婆抱以什麼樣的情感,是作為長女的責任感還是什麼,不過既然她不想糾結過去我也不去深究了。
在常去外婆家的那段日子裡我還小,只殘留著一些細碎的記憶。
記得那時候我通常是坐在院門口,媽媽給我搬張小凳子,讓我坐在上面看畫冊,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很幸運,很小的時候就擁有了各種好看的兒童讀物。外婆家有條看家的狗,每次我去了它都會趴在我腳邊,都說狗是會看主人臉色的,主人不喜歡的人它們是不會親近的,可那只黃色的土狗喜歡和我一起。
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坐在小凳子上看畫冊,旁邊趴著一隻小土狗,這個畫面作為我童年的一個標誌深深的印在我腦海裡。之所以這個場景會成為我人生節點上的一個重要標識,和我對那座房子和裡面的人的反感情緒無關,而是從那時起,「我是與眾不同的」這種信念開始在我腦中形成。
那時我經常會在外婆家門口坐上兩個小時,有小畫書看倒還算有意思,可以忘記外婆無視我的尷尬。村子裡有人經過時,會過來摸摸我的頭,說:「妞妞和你媽一樣愛讀書啊,將來肯定跟她一樣有出息」,「你媽有大學問,考上北京的大學呢」,「大學生的女兒就是不一樣,我兒子連字都還不識呢」等等,全是誇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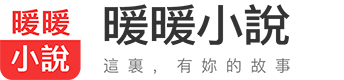



/0/1474/coverbig.jpg?v=f0803e778f362794e81fd331579e3d4d)
/0/9796/coverbig.jpg?v=1df0e27fa853b0ea6552821e0c773e5f)
/0/931/coverbig.jpg?v=f42bc6189328cba12c1db70a5cadcecd)
/0/78885/coverbig.jpg?v=83987c12490d70779a6fbe436b7457ec)
/0/385/coverbig.jpg?v=2d6b95a82b26c88e28ba5f1224240013)